民國103年7月19日
黃煒翔與我們相約,走一趟那個他自小成長,並成為他生命核心的某地──大直。
我想他已經自己一個人重遊故地幾次,在那些我們未曾和他熟識的時間裡,或是在心中「排演」過幾次,當他真的以一種重新記憶的心情回到這個地方時,該怎麼走,該怎麼說,該怎麼重拾明明記憶清晰卻又好像遺忘的過往,因為他的腳步,沒有一絲遲疑,帶我們一個場域一個場域的走過。
我們走進了內湖國小,在這個炎熱的暑假裡,操場沒有一個人,那個曾經是權威象徵的司令台,佈滿著枯葉砂石的荒涼。
他說,在某個下課的十分鐘裡,操場上大家在打躲避球、玩鬼抓人時,而他卻悄悄爬上司令台矇著眼睛,揣摩海倫.凱勒在黑暗中的感覺。
一起同行的國榮後來寫下:「煒翔的故事,聽起來超裝肖維的。但仔細想想,自己也不是沒有過,整天一個人龜在圖書館看武俠小說的日子,還興致勃勃地拉了一個朋友,一起寫武俠小說,那個朋友大概覺得我痴人說夢,完全沒在鳥我,結果大概寫一千字就不寫了。差別在於,煒翔已經在劇場演了十年的戲。現在,他要調整歸零,做一齣屬於自己個人的獨角戲。他的solo。而我一本武俠都寫不出來。十年來,大概都在喝酒,玩小鳥,當廢渣。人如果能在年輕的時候確立一件以上的事,或者是一件事,一件事就好。持之以恆地做,我非常羨慕。」
在操場臨接教室的地方有一個小水池,水都乾涸了,此刻的我們無法辨識,是因為放暑假將水抽乾,或是這個水池已經荒廢多年,等著歸來的故人。
他說,在畢業前夕,同學們要交小學六年和同學的生活照,作為畢業紀念冊的內容,他很少這樣的照片,於是只得事務性的補拍,和那些也要補拍的人一起。他被分配和一個他並不喜歡的人在「照片」中成為朋友,他很不開心,因為要將手搭在那個人的肩膀上,他還記得那樣的不開心,令人驚訝,因為我在他說完故事後試圖回想一個不堪的童年往事,卻一時半刻沒有一點想法。
於是我想看那張照片,那張封存12歲的黃煒翔的不堪的照片。
後來後來,我和他說起這件事,尤其是他還清楚記得每個小學同學的名字座號還有他們家住哪裡。
他說他其實也不能記得每一件事,這令他難過,為什麼分明是生命中的某個時刻的重要的事情,在幾年後,卻像什麼也沒發生過。
他想接著帶我們去教室看看,可是通往教室的走廊全被鐵拉門擋著,他看起來有些失望,於是我們找了一個可以看見校長室的位置,他問我們是不是能看見校長室,卻自己撇過頭完全不看,讓我們像傻瓜一樣地東張西望,總算是看見那些教室外的門牌。
他問我們,是不是能夠看見旁邊的牆上有著「禮義廉恥」四個大字,那個角度實在是難。
他說在那個日子裡,他總想人生中能夠遇到一個「知己」而他要帶他回來這裡,看著那「禮義廉恥」四個字的中間,有一個他小小的刻記,一個像是「米」字的刻記。
我們沒有看見,他也沒有。在我們心中,那個「禮義米廉恥」成為了某種,我們未曾參與的黃煒翔的童年的一塊幻象的拼圖,而對他來說,那是一個只剩下言說和文字的回憶故事,「米」還在嗎?他不知道,而記憶中那個禮義廉恥的模樣也變得模糊了,他會不會再來一次呢?和那個「知己」。話到了嘴邊,我沒有問,有些事情不問,很好。
我們在離開小學前,看見了籃球場上的籃球架。他問,你們有試圖灌籃過嗎?有啊!我們異口同聲地說,但是從來沒有成功過。
現在一定灌得到吧!國榮說著,朝籃球架衝過去,他飛躍起來,雙手抓在藍框上,回到地面時,整個籃球架都在震動,發出巨大的聲響。
這是一個時隔18年的灌籃。
這是一個時隔18年的舊地重遊,帶著小心翼翼保存的回憶與心情,不同於偶然路過的一時惆悵。
他說,如果不是帶著我們,或許沒有勇氣用這樣的心情在回來這個地方。
或許黃煒翔依然沒有找到「知己」,但他說在決定做SOLO的此刻,帶我們回來,對他來說意義重大。
我在20歲時,認識黃煒翔,至今也快10年了。
而我還想知道更多,關於這個記得全班同學名字座號住址,卻沒有知己的「黃煒翔」。因為在那些回憶裡,許多與未曾謀面的「我們」都相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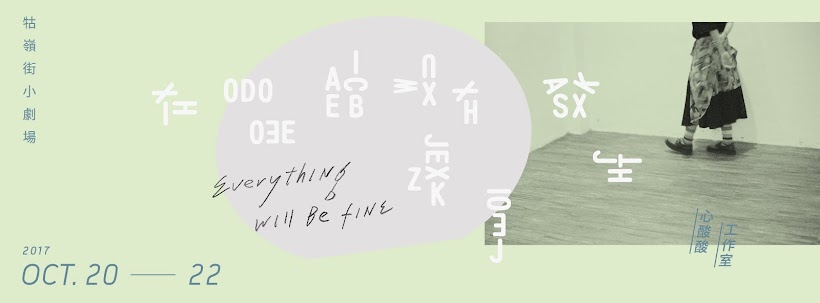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